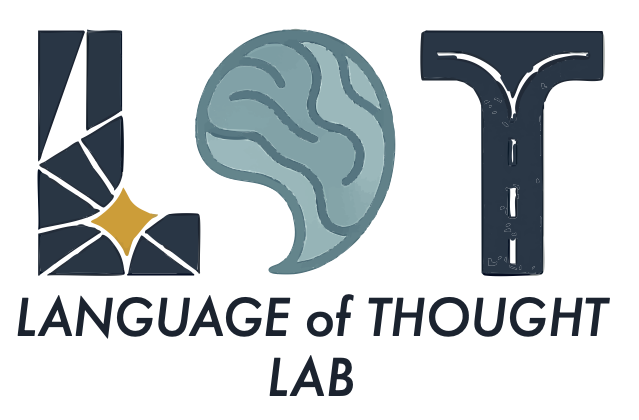《东方故事集》和世界模型
最近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短篇小说集《东方故事集》。全书篇幅不过五万字,却包含十个各具风貌的故事。它们没有办法用几句情节梗概来概括,因为每一个故事都自成宇宙。译者序中说,这是尤瑟纳尔未来创作历史小说的重要试笔。我在文字间确实感受到《苦炼》《哈德良回忆录》《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中的那种特质:场景浓烈、文字富于节奏感,仿佛口耳相传的神话,被作者娓娓道来。
译者指出,《东方故事集》有两大独特之处:一是题材的宽广,涉及多重东方历史语境;二是其中蕴含的哲理,尤其是那种难以分割的思辨力量。译者还总结作品的几个母题:爱情、母爱、虚构与创作。而在作者的后记里,尤瑟纳尔则特别强调书中首尾呼应的结构——她希望第一个故事和最后一个故事能成为互文的对照。“以消失与获救于作品中的中国大画家的目光,照见伦勃朗无名的同时代人,正悲哀地反思自己的作品。”
第一个故事讲述画家王福:他的画作真实到令皇帝错认。但当现实与画中世界出现落差,皇帝转而憎恶这虚构之力,并下令处死王福的徒弟。最终,王福以临终之作带着徒弟一同进入画里,逃脱了现实。最后一个故事则描写一位荷兰落魄画家:在他放弃绘画后,技术层面的平庸消散了,反倒获得了深刻的洞见。当邻居赞叹鸢尾花之美,说“上帝是宇宙的画家”时,他想到的却是人世的残酷丑恶,于是回应:“是的,上帝是画家,但不幸的是,他不仅画风景。”
我自己的体会是:无论是尤瑟纳尔对那些来自遥远传说的重新想象,还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都在指向一个共同的核心——个体的“世界模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模型,而故事展示了它们之间的碰撞与张力:
- 皇帝无法容忍真实世界与艺术虚构世界的差异,而责怪画家王福过分虚构;
- 伽利在灵肉分裂中,与自我模型失调而痛苦;
- “燕子圣母院”则展现了通过表达形式的转换,让不同模型得到调和。
换句话说,人类不仅能构建自己的世界模型,还能修正它、比较它,并与他人交换。这种能力最常见的体现就是故事——我们听故事、读小说、看电影,实际上都是在体验他人世界模型的方式。这也许正是智人认知革命的关键:掌握了虚构与创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