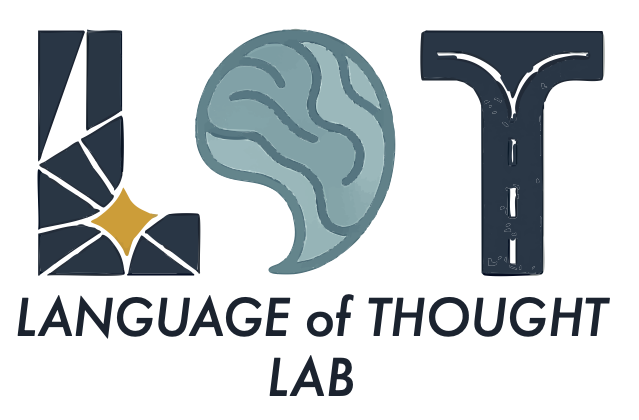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 确定性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确定性
最近读完了随笔集《维特根斯坦:从挪威的小木屋开始》。这本书融合了维特根斯坦的生平与哲学思想,梳理了他思想的演进轨迹,也融入了作者自身的阅读体验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长期以来,我始终难以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作品,尤其是那句被无数次引用的名言:
“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
这句话常被当作一种姿态——强调谦逊,表达对未知的敬畏。但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视角:这句话并非出于回避或神秘主义,而是直指语言作为工具的边界——语言无法承担一切表达的重任。
维特根斯坦的另一句话同样意味深长:
“人是人心灵的最好图景。”
很多感受并不能直接用语言描述,而是依赖非语言的方式传递。有时,沉默反而更能揭示那些不可言说的意图。
书中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语言的局限性:
- 托尔斯泰的小说比抽象论证更具感染力;
- 东北小伙舍身救人却被舆论漠视的事件,难以用几句感想总结;
- 诗句的魅力往往在于难以言喻的微妙,比如“春天融化了冰雪”与“冰雪在春天融化”之间的细微差异;
- 卡尔维诺通过塔罗牌的顺序讲述旅程,用非线性结构传达复杂经验;
- 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超越个体哀愁,触及宇宙与宗教感;
- 陀思妥耶夫斯基诉诸神秘主义与宗教,以回应科学主义带来的道德真空。
这些例子共同指向一个命题:语言是有限的,而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往往更贴近人类经验的核心。
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90后”作家刘楚昕在一次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他多次落泪,追忆已故女友,并引用了她的遗言: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
这种情感的冲击力,若仅通过文字呈现,远不如视频中那种直接的情绪传递来得真切而动人。语言在此显得迟钝,甚至多余。
书中进一步探讨了科学语言的局限性。科学语言追求清晰、确定、可验证,但它也无法超越自身的边界。维特根斯坦指出,所有语言都是一种“语言游戏”。如果我们执着于为每个概念提供清晰、唯一的定义,而忽视语言随语境与实践而变化的特性,就会陷入他所说的:
“理智的疾病。”
例如,在文学研究中并不存在严格的定义。正如一位北大德语系的朋友所说:
“如果一个事物已经被定义清楚了,那也就不值得研究了。”
在认知科学研究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界限。一项发表在 Neuron(Tomov et al., 2023) 的研究提出,人类在学习与推理中的表现,可以通过概率程序归纳(probabilistic program induction)进行建模。研究者设计了一类形式系统,能够在观察有限样例的基础上,自动推导出潜在的规则结构,并据此进行类比、演绎和问题求解。
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迅速掌握复杂游戏(如图形推理、操作规则或语法结构),并不是因为我们具备明确的逻辑演绎能力,而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心智中构建“解释程序”——一种对经验世界的生成性模型。
这个框架无疑是强大的,也令人兴奋。但它同时也暴露出一种更深的张力:我们始终是在使用形式化的语言,去近似表达非形式化的人类经验。
即便是概率程序这样灵活的工具,依然是在一个“确定性”的框架内,模拟“人类不确定性”的表现。我们试图用语言的游戏去模拟语言本身,用理性的工具去还原非理性的直觉,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式的努力。
维特根斯坦晚期思想的一个核心洞见也许正是:我们无法跳出语言之外谈论语言,就像我们无法站在梯子之外来描述它的结构。当我们试图为不确定性提供确定性的描述时,我们构建的,是一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一切最终指向一个问题:
我们试图用确定性的语言来描述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类心智与神经系统,
甚至用确定性的概率模型去解释不确定性本身——
于是构建起一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
但这样的解释,可以永远进行下去。
我们如何决定,何时应当停止?
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我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