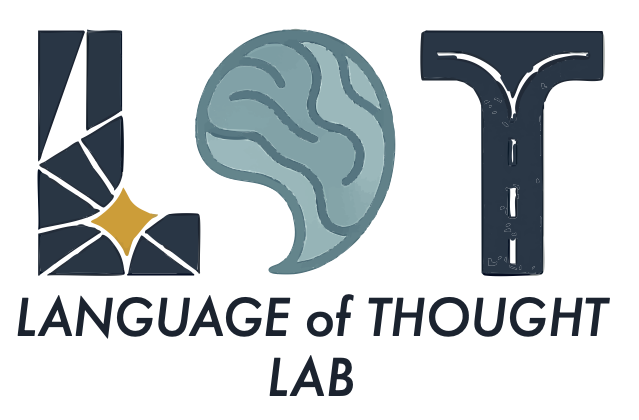理论科学 vs. 计算科学:两种研究范式的对比
作为一名物理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我经常会与从事理论物理的老同学交流。在闲聊过程中,我们常常比较理论科学与计算科学的研究特点与差异。我在此做一个简要总结。
一、基本偏好:理性批判 vs. 经验建模
理论科学家更偏好纯粹的理性批判。
康德曾说:“我并非意味着对书本或系统的批判,而是对普遍理性的批判,即对于所有能够‘独立于经验’而得出的知识。”
例如:
- 霍金关于黑洞辐射与黑洞熵的理论建模,并未依赖实验观测;
- 这种工作强调逻辑自洽与数学完备性,是延续爱因斯坦传统的第一流理论物理。
计算科学家则更偏向经验论与建模。
他们关注如何:- 基于感知与观测数据,描述未观测的隐变量;
- 从实验数据中提炼出具有预测能力的数值模型。
例如:
- 香农通过计算方式澄清通信问题,建立通信系统模型,并提出信息量的数学表达式;
- 这类工作是第一流的计算科学代表。
二、科学表达方式:定义 vs. 举例
- 理论科学家倾向于通过定义给出科学论断的最小内涵式解释。
- 计算科学家更喜欢通过举例呈现科学论断的外延式意义。
这也反映了 reasoning(推理) 与 inference(推断) 的区别:
- Reasoning 更关注理论框架的整体建构,整合多个 inference,进行系统性推理;
- Inference 是基于已有证据对隐藏因变量进行的推断,是 reasoning 的一个子集。
三、对“简洁科学”的不同态度
理论科学家通常认为,最有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应具备:
- 可以形式化为微分方程;
- 具有低维结构,可用于有效预测。
因此,仅依赖简单 AI 模型进行数据拟合,其科学价值往往受到质疑。
尽管这类模型可能具备预测能力,但它们未能揭示底层结构或机制。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方法尝试融合理论与计算的思路,在维持预测能力的同时引入结构表达。
其中代表性方向之一是:
将建模对象从“变量之间的映射”拓展为“函数空间之间的映射”,
即直接学习微分方程的解算子,是理论建模与数据驱动的结合。
例如:
Neural Operator:一种建模偏微分方程解算子的通用方法。
Kovachki, N. et al. Neural Operator: Learning Maps Between Function Spaces. arXiv (2021).
doi:10.48550/arXiv.2108.08481
该方法的优势在于:
- 在函数空间层面建模,具有离散化不变性;
- 能够捕捉低维结构的解算规律,提升物理解释力与泛化能力。
但在某些系统中也存在局限。例如:
- 在量子力学中,变量描述(薛定谔方程)与算子描述(海森堡矩阵*是等价的;
- 二者在建模复杂度上没有本质差异,因此是否采用算子建模不一定带来优势。
换言之,Neural Operator 是理论结构与计算方法结合的有力工具,但其效果依赖于具体系统是否存在清晰可提取的结构,且该结构是否可被数据驱动方法捕捉。
四、研究习惯的差异
理论科学家:
- 更倾向于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一个问题;
- 在灵感消退前取得重要突破;
- 合作交流中,强调留出“共同沉默思考”的空间,专注攻克具体问题。
计算科学家(我):
- 面对更长的研究链条,习惯并行推进多个课题;
- 强调明确分工与进度追踪;
- 避免低效会议,优先传达具体、明确的想法。
总结
这两类科学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文化:
- 一类从纯理性出发,强调理论自洽性与形式完备;
- 另一类从数据与假设出发,关注模型结构与实际应用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