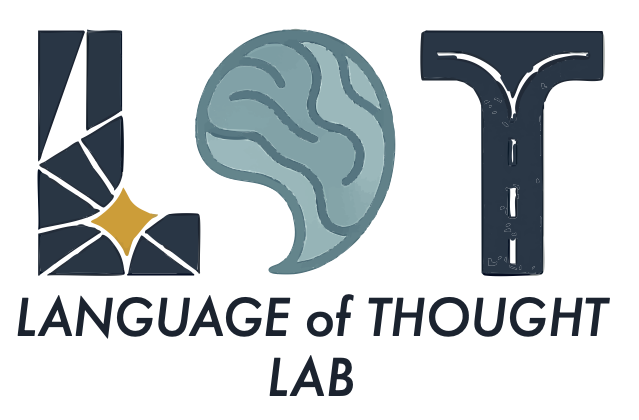知识是几何的,还是代数的?
晚饭时和一位本科学数学的同事聊起物理系和数学系的本科教学。我们意外发现:数学系约有 80% 的课程围绕代数结构展开,而物理系却更强调几何直觉——例如用“场”的概念来理解那些其实可以被代数表达的动力学方程。
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知识的本质,是几何的,还是代数的?
我们从婴儿的行为开始思考。观察一个婴儿如何与世界互动,会发现他们的认知方式似乎天生偏向几何。他们活在一个立体的、连续的空间中,看到书本上的图片,第一反应是伸手去触摸,仿佛要将二维图案“揉成”三维实体。他们用身体与世界建立空间关系,而非操作抽象符号。
而反观人类的教育系统,尤其是数学教育,却是高度代数化的:从认识数字、学习加减乘除,到函数、不等式,再到大学阶段的微积分与线性代数。几何,反倒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块,而非主干。
这似乎在暗示:我们天生以几何方式感知世界,却后天以代数方式传递知识。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智能体的“初始知识”或许就是几何式的:连续的空间感知、方向感、距离判断——这些可能作为某种先验结构,被“刻入”基因。而代数,则是我们在知识传承的过程中,为了高效、稳定、可重复地编码信息而发展出的人工语言。
如果我们的神经系统中存在知识的表征机制,那么它们的形式会是几何的,还是代数的?
认知神经科学中已经出现一些初步的线索。例如:
认知图谱(Cognitive Map)
Behrens 等人(2018)提出,大脑通过低维的“地图结构”来组织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几何化知识表征:概念之间的“距离”在空间中是有意义的,学习就是在图谱中定位与导航。贝叶斯大脑(Bayesian Brain)
Pouget 等人(2013)则认为,大脑通过神经活动实现了某种形式的贝叶斯推理。这种模型强调代数式的计算过程,通过概率密度函数与条件概率来进行信息更新。
这两种模型,分别代表了**知识几何化(spatialized)与知识代数化(formalized)**的两种路径。
进一步设想:我们是否可以在跨物种的神经研究中发现类似证据?比如,非人灵长类动物是否更依赖几何直觉进行认知,而人类则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将其转化为代数结构?或者,更激进地说——代数只是知识在历史中得以存续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人类的思维本质上始终是几何化的。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对“认知革命”的定义。他认为,认知革命的标志在于人类开始讲故事、虚构概念、想象不存在的事物,由此形成了宗教、国家、商业等超个人的秩序体系。
但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这场革命?
或许,认知革命也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开始以几何与代数的方式表达知识。
几何,是对空间直觉的抽象提炼;
代数,是对逻辑结构的语言编程。
故事使我们联结,代数使我们传承,几何使我们理解。
如果真是如此,当脑机接口技术日益成熟,我们是否可以跳过代数的中介,直接通过几何方式传输知识?
知识的表达方式,是否也有技术史?
参考文献:
- Behrens, T. E. J., et al. (2018). What Is a Cognitive Map? Organizing Knowledge for Flexible Behavior. Neuron, 100(2), 490–509. https://doi.org/10.1016/j.neuron.2018.10.002
- Pouget, A., Beck, J. M., Ma, W. J., & Latham, P. E. (2013). Probabilistic brains: knowns and unknowns. Nature Neuroscience, 16(9), 1170–1178. https://doi.org/10.1038/nn.3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