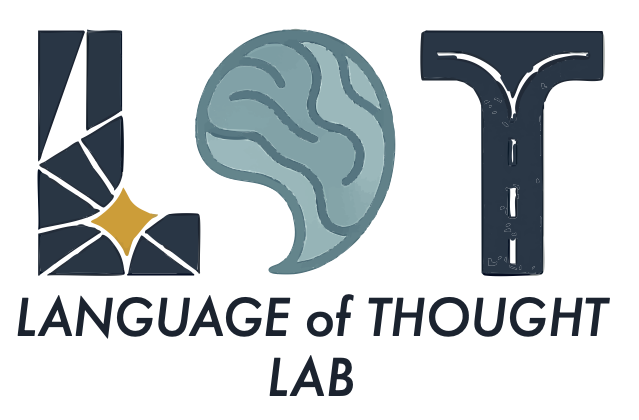You need to distract, then you can …
这两天晚上看《十三邀》,看到对伍迪·艾伦与傅高义的访谈,有一些感触。
在伍迪·艾伦那一集中,有位年轻的脱口秀演员谈到自己的观影体验。他说,伍迪·艾伦的电影总喜欢“抽离”——他会轻轻触及一个严肃的主题,然后迅速转身离开,让人不至于沉重,却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伍迪·艾伦自己对这种创作方式也颇为坦然。他说写剧本对他而言不是痛苦的事,一个“还不错(decent)”的剧本,只需要十几周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他不执着于打磨完美,也不沉溺于主题的重量,而是始终保持轻盈。他曾说:
“Distraction is the best medicine.”
对他来说,you need to distract, then you can move on.
傅高义的访谈也令人印象深刻。许知远问他如何找到宏大而独特的问题来展开研究,他的回答也充满“抽离”的意味。他说自己从不执着于某个问题,而是从小角度切入,保持随时可以抽离的姿态,反而更容易找到抽象的维度。
他对当代社科学术圈日益细节化、文献化、数据化的倾向感到失望。这些细节的堆积,反而让人忽略了真正重要的宏观问题。对他来说,是:
You need to distract, then you can abstract.
这种“抽离”的态度,也出现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他称之为防止刻奇(kitsch)。刻奇是一种对沉重的刻意追求,是对情感的套路化渲染。它让艺术变得平庸,让思想陷入空洞。要拒绝刻奇,就要学会抽离,保留某种轻盈与距离感。
我还想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习惯。他每天在课堂上沉浸于自我对话与哲学思考,而每天晚上,他会去电影院看最通俗的喜剧片。不做解读、没有目的,只是简单的感受。在抽离中恢复,然后重新专注。
You need to distract, then you can 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