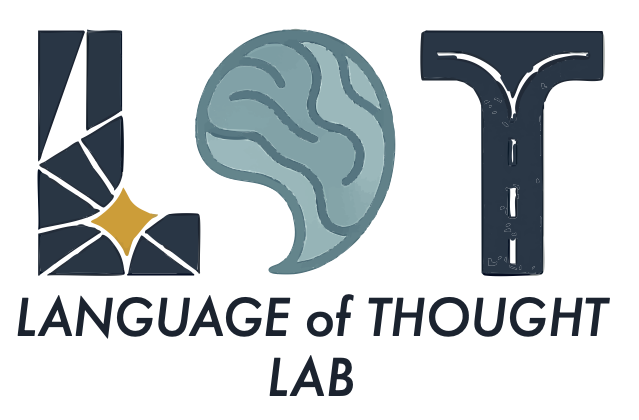主动感知和冥想
一起组织 Journal Club 的意大利朋友即将回家乡工作,我们聚餐聊了三个小时,期间有几个想法值得记录。
我们从 active inference 的主题切入。Karl Friston 在教材里列出了两条理解路径:
- low road:从传统的贝叶斯推断出发,以数学框架为核心;
- high road:从生物系统的第一性原理出发,认为自组织系统的关键在于引入噪声,并在噪声中持续降低“惊喜”(surprise minimization)。
我的朋友更喜欢 high road,因为它建立在更简单的起点假设上。
由此,我们谈到冥想。他提到一位朋友刚参加完冥想夏令营:完全断绝外界联系,每天按时进行无输入的冥想。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原本通过日常事务分散注意力来化解的负面情绪,在冥想中被反复唤起,最终让他陷入抑郁。
从 active inference 的角度看,冥想是一种与日常“信息过载”相反的噪声。人们试图在这种白噪声般的放空状态下不断降低惊喜,从而收敛到新的稳定状态。但如果已有的世界模型过强,那么白噪声的力量很快就会被淹没,难以起效。
我由此提出另一种设想。
古代中国人在稳定的精神结构里生活,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提供了日常秩序。但近代以来,西方的多样思想涌入,打破了这种稳定,使得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出现了无数精神试验。于是,除了“冥想”,另一种疗法或许是相反的——反冥想:将信息过载推向极致。
- 平时看一个短视频,在反冥想中,就看十个,还要同时复述;
- 平时看一部剧,在反冥想中,要把十部剧的剧情强行拼接成一个完整故事。
这种“有结构的噪声”,可能比单纯的白噪声更具冲击力,也更能打破个体固化的习惯状态。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方法戏称为 《好梦一日游》,署名:电影《甲方乙方》。